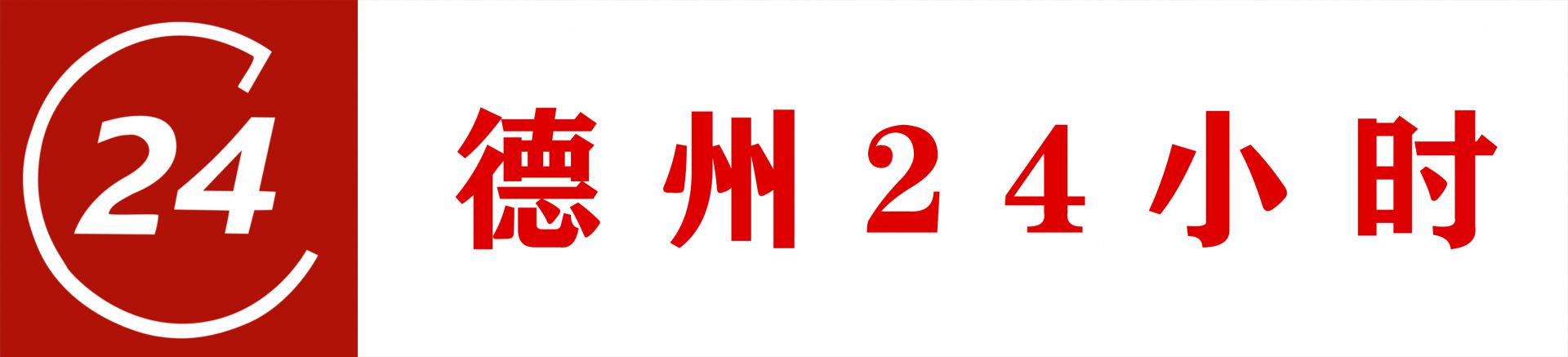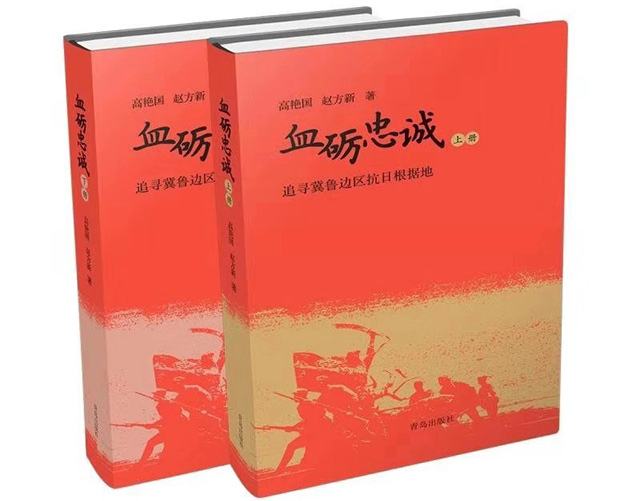
冀鲁边平原真正的“冬天”是从1939年秋天正式开始的。
正驻扎在鲁南山区一个山村的周贯五接到萧华一封电报,命他立即返回冀鲁边。周贯五凝望着山坡上黄灿灿的树丛,半晌无语——对他而言这个决定太突兀了。他记得当初六支队七团离开冀鲁边时,很多当地的战士泪水涟涟,磨磨蹭蹭,走出好远还拧着脖子回头张望,更有人偷偷地抓一把泥土装进衣兜里,“老人们说到了外地好水土不服,用老家的土冲碗水喝就没事了”。他心里何尝不是满满的留恋!冀鲁边这一年里每个日子都有棱有角、有声有色,尽管这里的风比南方粗粝得多,这里的雨不如南方温存,这里的小米干饭没有南方的大米温软可口,然而这片土地已经牢牢牵住了他的魂儿,因为这里驰骋着他的金戈铁马梦,这里埋葬着众多亲如手足的战友,这里生活着600多万多灾多难的乡亲……几个月间,他和团长李子英、政委崔月楠带着队伍,跨过津浦铁路,经茌平,过东阿,渡黄河,历平阴,到肥城,跟先期到达的孙继先部接上头,面聆了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的指示,然后继续南下,游击于泗水、平邑、新泰、蒙阴一带,棒喝了山东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的特务大队,收编了五个大队的红枪会,击退了3000多日伪军的骄横进攻。从平原融入山区,七团携带着万钧雷霆,遇贼杀贼,逢寇灭寇,顾盼间凛凛生威,昂首长啸,山呼林应。这种感觉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如鱼得水”吧……可是,现在屁股还没坐暖沂蒙山的板凳,就得重返冀鲁边了,心里多少有点小别扭——后来,周贯五经常跟身边的人说:“我这人啊生来就是个‘车轱辘命’,所以常被抓差去应急……”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更是党的纪律性,周贯五二话没说,带上仉鸿印、警卫员和骑兵班上路了。
一听重返冀鲁边,仉鸿印乐得合不上嘴:“哈哈,又要见到那些老兄弟啦!”
周贯五打趣他:“老仉,不光是想老弟兄们吧?”
仉鸿印的脸腾地红了:“哎呀!周政委,你这么个老实人也会说风凉话啊!”
周贯五说:“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嘛,家里的妻儿老小,到哪里都是咱们撂不下的牵挂啊!”
仉鸿印说:“这倒是实话,可俺老仉自从参加八路军,就没那么多儿女情长啦,一心想的就是多杀鬼子,早日还老百姓一个清静年岁。”
周贯五说:“老仉啊,这次返回冀鲁边虽然还没交代什么任务,我看得做好扛硬活的心理准备。你想,主力部队撤出后,边区的情况大不如前,日伪军的蚕食更疯狂了,国民党的顽军趁机又开始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所以回去可不是叫咱们享清福。”
仉鸿印昂然答道:“大丈夫以身许国,俺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到时候有什么最困难的事,你就尽管交给俺吧,俺老仉要是眨眨眼打个哏儿,还咋有脸在你跟前杵着呢?”
周贯五哈哈大笑:“你老仉说话就跟打山炮似的,带劲儿啊!”说完“啪”一鞭子,胯下的灰马一个箭步向前跃出,在溶溶月色里像一朵云彩被狂飙吹远。仉鸿印双腿一夹马腹,他的坐骑咴咴两声嘶鸣,山林簌簌,空谷嗡嗡,耳边风声顿起,不一会儿就冲到了这支小分队的前头。嗒嗒的马蹄声穿村过店,许多人在梦里见到了月光河上徐徐绽放的白莲花。
1939年阴历八月底、阳历十月上旬,周贯五一行重新踏上了冀鲁边根据地的土地,这时他才知道边区的冬天其实早在秋天时就已经降临了。
他们最先见到了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李广文。李广文激动得眼圈里汪着泪水,握住周贯五的手很长时间没放开:“周政委,你们走了以后,咱边区的日子甭提多艰难了。”
周贯五说:“这样吧,你带我们先去找符竹庭主任,边走边说。”
李广文说:“现在符主任正在宁津呢,说是等你一到,他就带着队伍转移走。”
周贯五说:“事不宜迟,现在就走吧。”
路上,李广文给周贯五和仉鸿印讲了冀鲁边几个月来的变化:从去年秋天开始,边区先是遭遇三十年未遇的特大旱灾,旱得田地裂出一道道口子,大片大片的庄稼干枯绝产;接着从天津卫南洼的芦苇滩里飞出来的蝗虫遮天蔽日地过来,庄稼被啮噬得只剩下光秆。老百姓呼天抢地,只能以树皮、粗糠充饥,情急之下,也把扑杀的蝗虫拿回家,当粮食煮了吃;今年春上干旱还在持续,好不容易到了六月,下了一场透地雨,赶紧抢播上玉米等秋季庄稼,盼着换换年景,没想到临近中秋节,气温骤降到零度以下,一夜之间,“霜冻之锤”把正在孕育果实的玉米锤打得败絮一般,遍野的破破烂烂,惨不忍睹,有人在田头号啕大哭,更有人觉得无望,拉着打狗棒远走他乡……
李广文沉痛地说:“周政委,你不知道,老百姓为了活命,只好把没熟的棒子掰回家煮着吃,或者晒干了,碾成粉,蒸团子吃。这东西甭提多难吃了,又苦又涩又硌牙,难以下咽不说,拉还不好拉呢,费劲巴拉都是带着血拉出来的。”
周贯五的眉心越绾越紧,他没想到边区的生活这么艰苦,重重地叹了口气。
李广文忽然愤慨地说:“老百姓这样的年景,日本鬼子和‘二狗子’还是该怎么征粮就怎么征粮,逼得很多人家卖儿卖女,上吊跳井,快把边区变成人间活地狱了。”
周贯五说:“这也正是我们主力部队转移的一个原因,我们不能再给老百姓雪上加霜了——这段时间日伪方面有什么动向吗?”
李广文爆粗道:“这群王八蛋可是张狂到天上去了!他们不光占了边区的全部县城,还到处修据点,挖封锁沟,设关卡,把各县、区分隔开,一口一口蚕食咱根据地,吃得要多甜欢就多甜欢!原来咱们根据地就像一张大饼,现在被鬼子分割得一块一角,零零碎碎的。二鬼子也更嚣张了,每天狐假虎威地出来骚扰老百姓,抓捕我抗日军民,气死个人!这些狗东西,早晚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周贯五陷入沉思,冀鲁边的形势明显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甚至有点倒退回三十一支队时期的模样。
萧华带队转移后,符竹庭担任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书记,全面主持边区工作。
周贯五大踏步向符竹庭走去,两人亲热地握手后,符竹庭说:“老周,我估摸着你这几天到,所以早就打好了行李,准备你一来我就走。”
周贯五不解地问:“这是干啥?好像俺老周是专门来撵你似的!”
符竹庭哈哈大笑:“我得给你这路神仙倒个地儿啊!”
周贯五也哈哈大笑:“我还想跟你联手在边区鼓捣点大动静呢,是不是有更重要的任务安排了?”
符竹庭说:“师部决定让我到鲁南开辟新根据地,让你回来坚持斗争,领导整个边区的工作。”
周贯五有点懵:“不可能吧!我寻思萧主任让我回来是配合你工作的,即使你离开边区,也是别的同志顶上去,我的能力不够啊!”
“老周啊,组织上既然这样决定,肯定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你说你能力不够,你说谁还比你更适合?你对边区的情况熟,跟边区的同志搞得热络,威信高,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水平都是一流,上级领导没看走眼。”
“我还真不是谦虚,我是怕自己干不好,耽误了党和人民的大事。”
“别再推辞了,现在边区环境艰难,就需要你这种有韧劲的干部,再说现在决定已经出来,你老周就是有一箩筐的理由也没有用,还是抓紧熟悉情况,走马上任吧!”
周贯五无话可说。
夜里,周贯五辗转反侧,思如潮涌,过去在冀鲁边区的情形一幕幕划过脑海:东进纵队刚刚跨过津浦铁路时自己那个兴奋劲儿,穿行在大平原青纱帐时心底生出的万丈豪情,初入边区时老百姓送来的一篮篮鸡蛋、红枣、花生,一双双“千层底”,一件件“老粗布”,每到一村乡亲们总是腾出最好的房间给部队,无棣县的刘大娘亲手把五个子女送进挺进纵队,还有无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抗日干部和子弟兵……
有两个问题横亘在他的心头:冀鲁边根据地要不要坚持下去?能不能坚持下去?
前一个问题看似不成问题,但在主力部队撤走后,却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目前边区仅有六支队八团一、三两个营和津南支队、运河支队各一个营,以及由挺进纵队直属队的一个连和陵县地方武装组成的鲁北支队,共1600多人,而要面对的则是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自然而然,大多数人心里就会升起这样的疑团:冀鲁边区根据地还有没有必要坚持下去?如果有必要,就不该把主力部队统统抽调出去,因为让留下的力量来支撑这样的局面无疑是极为艰难的。但这个问题对周贯五来说是无须思考的,因为组织上让他重返冀鲁边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而且,很快他就接到了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政治部主任萧华的指示:要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冀鲁边。冀鲁边根据地绝对不能丢失。它是清河区的屏障,也是我党发展抗日武装的兵源基地。它牵制了日军两个联队3600余人,牵制了伪军15000余人和顽军10000余人。没有这块战略基地,我们在冀鲁平原的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据。
对于第二个问题,马振华给他的答案是:“边区的群众基础好,有革命斗争传统,地方党和部队也非常团结,坚持边区斗争准能行。只要大伙有决心,依靠党,依靠群众,坚持武装斗争,我们完全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周贯五又接触了一些留在边区的同志,大家的态度都很坚决,他悬着的心慢慢踏实了。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符竹庭率挺纵政治部机关登程开赴鲁西。同时,邢仁甫率挺纵六支队二营和特务营开赴鲁西东阿县一带。据李启华回忆,“这时邢仁甫惊慌失措,竟随符竹庭撤走,将专署机关也带走了”。从李启华的表述看,组织上事先并未安排邢仁甫撤离,是他擅自决定跟随符竹庭撤出冀鲁边的,因为走得匆促,竟连应属地方组织的专署机关也带走了。他的这一做法当时就引起了一些人的腹诽。
周贯五怅然若失,那一刻,忽然觉得肩头一沉,下意识地扶住身旁的一棵老槐树。马振华、李广文、仉鸿印等人脸上也流露着依依不舍之情,此一别隔山隔水,隔着炮火硝烟,隔着人生际遇的神秘莫测,怎不让人牵肠挂肚?
目送符竹庭和部队渐行渐远,马振华顿觉心里空落落的。
他跟李广文商量:“广文啊,符主任只交代他走后由周贯五同志负责边区的工作,但具体领导班子组成也没定下来,很有必要再找他明确一下。”
李广文一听:“对!对!这是个关键性问题,必须明确下来!”
马振华说:“好在大部队走不快,我带几个人追上去问问。”
李广文说:“挑几匹脚力好的马。”
当天傍晚时分,策马飞奔一天的马振华在津浦铁路东赶上了符竹庭。
符竹庭笑眯眯地看着他:“马主任,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这是要把我送到鲁西啊!”
马振华气喘吁吁地说:“符主任,有件重要的事情忘了问你。你离开后边区的领导班子怎么搭啊?这事刻不容缓,关系着边区的命运,所以我赶紧追你来了。”
符竹庭一拍额头:“哎呀!光顾着忙转移的事了。根据组织上的决定,周贯五同志担任冀鲁边军政委员会书记,其他领导成员的搭配,由他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马振华又问:“杨靖远同志牺牲后,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第六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的职位一直空着,能不能也由贯五同志兼任?”
符竹庭说:“我同意你这个建议。”
…………
马振华连夜赶回宁津县驻地,拂晓前叩开了周贯五的门,陈述了见到符竹庭的情况,一大早又召集了党政军方面的负责同志,传达了符竹庭的指示。边区的领导班子就这样基本确定下来了。
符竹庭带着这支在冀鲁边的大熔炉中淬炼出的精锐之师,从鲁西到鲁南,再到滨海地区,东征西战,出生入死,创建了横跨苏、鲁两省的滨海区抗日根据地。1943年11月26日清晨,日军偷袭滨海军区机关驻地赣榆县黑林乡马家旦头村,符竹庭指挥部队反击,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当时大雾弥天,符竹庭见敌人败退,策马追杀,不料头撞在村寨大门的门框上,跌落马下,虽经全力抢救,他生命的指针还是永远地停止在31岁上。
1940年3月底,周贯五主持在宁津、乐陵交界处的鬲津河南岸丛林地区相继召开了三次全区性的会议——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部队指挥员和骨干战士联席会议以及军政民三方联席会议。周贯五以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第六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的名义,在会上做了主题报告,解释了主力部队撤离边区的原因,指出了边区坚持斗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号召大家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并对下一步的工作做了部署:一是进一步加强党、团、群众组织的建设,广泛地宣传,进而发动和组织群众;二是巩固以宁津、乐陵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逐步向外围发展,深入敌人的后方去,把敌占区变为我军的游击区和根据地,造成有敌人无敌占区的局面;三是加强县大队和区中队的建设,发展武装,扩大队伍;四是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开明士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参加抗日。总的口号是:“恢复元气,振兴边区!”
同时对军队做了具体的部署和分工:鲁北支队继续在鲁北活动,负责破坏德州以南、黄河以北的津浦线,保持跟鲁西根据地的联系;六支队八团一营活动于渤海沿岸的盐山、新海等地,相机袭扰天津;津南支队活动于南皮、沧县、青县一带;运河支队在东光县东部、南皮县南部、吴桥县北部地区坚持斗争,开辟根据地;六支队八团三营的十连、十一连、十二连及新编第九连,由杨承德指挥,到盐山、新海、无棣、阳信、济阳、商河一带开展工作;六支队八团三营九连、东光青年连和庆云县县大队合编为特务营,负责保卫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
对于严重的粮荒,军政委员会通过实施减租减息,合理摊派捐税,开展凿井抗旱,向地主借粮,组织运粮队外出采购粮食等措施,大大缓解了灾荒,人民菜色的脸上又有了笑模样。
边区军民的情绪稳定下来,二十几个县相继恢复和健全了县委、县政府和各种群众团体组织,掀起了一股青年人参军的热潮,队伍不断壮大。
仉鸿印从鲁南回来后,周贯五让他利用人熟地熟的优势重新组建津南支队,由他任支队长,李恒泉任政委。老仉拉队伍的消息一传开,盐山、乐陵、宁津一带的青年们背上干粮袋连夜来找他,到1939年10月,组建起了包括五连、六连、七连、八连,外加两个手枪队,总计300多人的队伍。其中五连骁勇善战,全部日式装备,头戴钢盔,成为在冀鲁边区令敌伪闻风丧胆的“铁帽子五连”。
队伍刚刚筹建起来,最缺的就是枪支弹药。仉鸿印没少为这方面发愁。1939年秋,日军抓来民夫在旧县镇据点附近修路架桥,由一个小分队担任警戒,大概他们以为八路军早被吓破了胆,平时警戒时就把步枪搭成枪架,空身在工地上溜达,只在一个土台子上架着一挺机枪,三个日本兵守着说说笑笑。仉鸿印得到情报后就把主意打到了这伙日军身上。他派手枪队的一个班化装成民工混进工地,派两个连埋伏在公路两边的青纱帐里作掩护。
第二天,日军工地上出现了一个黑脸大汉,袒胸露腹,憨头憨脑,但在他蹲下去喝水、跑到路边解手时,那双眼睛可就叽里咕噜地活泛起来。他傻乎乎地靠近日军的机枪,憨憨地问鬼子:“太君,这是什么的干活?”
日本兵呵斥:“开路,开路,那边的干活,这边的不行!”
黑大汉“啪啪”拍拍胸脯:“我的力气大大的,力气大大的!太君你看看的干活。”说着,他弯腰扛起一根两个人抬都吃力的木头送到桥头,边走边故意扭着秧歌步,看得日本兵前仰后合:“你的大大的好玩!”
黑大汉来回扛了几趟,不断变换着步伐,面部表情也越来越滑稽,几个日本兵笑到肚子抽筋。黑大汉装作歇歇的样子,再次靠近机枪,一手撩起衣襟扇着汗,一手碰碰机枪身子,似乎被电着一样赶紧抽回来。日本兵指着他:“中国人傻瓜,傻瓜中国人!”
黑大汉再次把手放在机枪上,似乎胆子壮了,摸了摸,然后拍了拍,见也没什么情况,望着日本兵傻笑,意思是这东西敢情不咬人啊。日军通过“心灵之窗”也读懂了黑大汉的心理活动,又拍着手笑了。黑大汉似乎受到了日本兵的鼓舞,竟把机枪扛上了肩头,接着夸张地学着日军操练的样子高抬腿、踏步走,嘴里喊着“一二一、一二一”,惹得日军笑成了一团。
黑大汉扛着机枪喊着“一二一”向青纱帐走去,开始日本兵还把他当作玩笑,等他钻了进去,等一会儿也没出来,才大呼小叫起来,刚追到地边,里面一阵排子枪,打得日军吱呀乱叫、抱头鼠窜,回身去找枪。我化装成民工的手枪班战士早就把那些步枪收缴了。一眨眼,十几个鬼子全见了阎罗。津南支队战士随之消失在随风起伏的青纱帐里。
那个黑大汉正是手枪队队员韩凤池。
1940年5月初,杨柳新正带着六支队八团一营游弋于鬲津河北岸旧县、荣庄一带,接到周贯五的命令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日伪方面大肆散布八路军出逃冀鲁边区的谣言,动摇我边区军民的抗战信心,为此命你营在条件有利时主动出击,狠狠打击日寇一下,告诉群众我们不但没有离开冀鲁边区,而且还在顽强抗击着侵略者。
杨柳新把周贯五的命令告诉了营教导员贾乾瑞。
贾乾瑞说:“目前我部准备东进盐山、新海、无棣接合部,正好可以在走前敲打一下小鬼子。”
杨柳新说:“好长时间没打仗,战士们的手都痒痒了。”
贾乾瑞说:“我刚从盐山县大队那里了解到,距此不远的小马家据点的鬼子最近很猖狂,隔三岔五就出来‘扫荡’,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祸害老百姓,不行就拿他们开开荤。”
杨柳新说:“小马家据点周围都是鬼子和二鬼子的据点,这一仗既要打得解气,还得打得巧。”
贾乾瑞说:“杨营长,是不是已经有什么妙计了?”
杨柳新神秘兮兮地一笑。
5月4日,八团一营驻进盐山县前堂村,无棣、盐山两个县政府机关,县大队和边区锄奸团驻进坊子、后堂两村。杨柳新、贾乾瑞带着警卫员围着村子转了一圈,下令构筑工事,部署兵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地西距小马家据点仅6里地,东北距黑牛王据点6里,东南距庆云据点7里,北距望树据点10里,可谓“自投罗网”于敌人的包围圈。
早有密探把情报传给了小马家据点的日军曹长森田,说发现八路军的盐山县大队在坊子村一带出没。森田一拍桌案:“土八路竟敢在大日本皇军眼皮底下活动,太目空一切了,必须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遂令据点里的200多名日伪军倾巢出动,乘坐30多辆骡马车,杀奔坊子村。在坊子村外的田野里,盐山县大队在县长崔益民带领下象征性地跟日军交交火,旋即掉头逃跑。森田见盐山县大队只有四五十人,衣服破烂,装备落后,一触即溃,撇撇嘴:“土八路的不经打,速速追击,务必围而歼之。”
盐山县大队退至前堂村,穿村而过,迅疾埋伏到村外的野地里,静待敌至。森田紧追慢赶,到了前堂村西,趾高气扬地向村里走去,距离村头只有三四十米时,一阵炒豆似的枪声响起来,打得日军的骡马车乱了套,如没头的苍蝇般乱窜乱撞,当即倒下几十人。森田一听枪声就知道遇到了八路军的主力,脸唰地白了,急令部下寻找有利地形反击,同时派人向近处据点求援。日军车队领头的骡子车,赶车人正好是前堂村人,枪声一响,骡子受惊,左右摇摆着身子,赶车人趁机猛踢骡子的肚子,骡子惊怒之下,甩开四蹄拉着一车弹药向村里窜去。八路军战士拦下骡子,笑纳了这笔“意外之财”。
前堂村西是一片开阔的洼地,日军被我火力压在路边的道沟里。森田躲在一辆掀翻的马车后指挥着日伪军向村里进攻,但日伪军一爬出道沟就置于无遮无拦的境地,还不由着我方火力欺负啊。杨柳新在一片芦苇地里瞭望着敌人的动态。森田见强攻损失太大,发现道沟旁有几座坟头,就让人去抢占,准备以此为依托,跟我方展开火力对峙。杨柳新发现了敌人的意图,命左右两挺机枪交叉封锁路线,日伪军屡次冲向坟头都被截击回去。森田气得两眼血红,刚一冒头,耳边飞过一颗子弹,掀掉了他的军帽,吓得赶紧缩进掩体。
中午过后,前堂村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枪声,来自周围据点的日伪军遭到了我预设打援部队的阻击,裹足不前,眼瞅着森田的部队就在不远处,愣是没法会合。杨柳新战前的部署是由盐山县大队诱敌深入,进入我方一营四连伏击阵地,予以痛击,二连埋伏于村南迎击南面之敌,一连和无棣县大队负责东面和东北面来敌。因为我方做足了功课,工事构筑得很坚固,敌人反复冲击均无功而返,反倒扔下一具具死尸。
杨柳新密切关注着四面的战事进展,对通信员说:“告诉同志们,不要手软,不要稀罕子弹,给我狠狠打!”
贾乾瑞递给他一支烟,点上,说:“老杨,这样胶着下去,敌人的援军会越来越多,我们得考虑撤出战场了。”
杨柳新推推帽子,喷出一口烟,瞧瞧西斜的日头,说:“别担心,老贾,天黑了咱们再走,论起走夜路,小鬼子跟咱们可不是一个档次,咱们八路军个顶个都是走夜路的祖宗!”
贾乾瑞说:“我们这一仗等于封住了小鬼子的嘴,他们再嚷嚷八路军逃跑了,三岁小孩也不信啦!”
沧县日军炮队随着暮霭的降临开到了前堂村,四面的枪声渐渐停歇下来,日伪军在夕阳的余晖里构建工事,意欲困住八路军,明天一鼓作气,予以歼灭。
杨柳新让通信员传令给各部,我军已达到战略意图,可以趁夜色伺机撤出战斗。
日军放出了严密的岗哨,幽灵一般围着村子游弋。敌人点起的火堆几乎连成了一圈,紧紧锁住了前堂村。凌晨的寒气依然凛冽。一支悄悄移动的队伍像锋利的刀片,从日伪军构筑的防线罅隙间穿过,向北运动一段距离,再折而向南,重新回到荣庄一带,美美地睡上一个回笼觉。
森田满腹狐疑地看着空空荡荡的八路军阵地,百思不得其解,嘴里咕咕哝哝着什么。
跟在他身后的一个伪军头目,赔着一脸肥嘟嘟的笑,低声下气地劝着:“太君,不要着急,八路的跑不远。”
森田胸脯起伏着:“八路的会飞?”
伪军头目凑过脸来:“不是飞,是土遁。”
森田问:“土什么遁?”
伪军头目说:“太君,您不知道中国古代有个人叫土行孙吗?能钻进地下走路。”
森田怒道:“八嘎!你的胡说八道!”“啪”抡圆了一个耳光,把对八路军的怨气结结实实撒在了伪军头目身上,打得他就地转了几个圈。
前堂一战,我军在人员、装备均处劣势的情况下,主动出击,与敌苦战10多个小时,以极小的牺牲,歼灭日伪军80多人,是挺进纵队主力转移后边区部队取得的第一个胜仗,大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日士气。
在许多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文章中,对于1940年的印象大都用了“窒息”两个字来表述。这种“窒息”首先来自中日战场上沉闷的对峙局面和汪精卫伪政府的“还都”南京。而更严重的“窒息”则来自日军对中共敌后根据地的窒息政策——“囚笼战术”。日军对占领区的统治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上层层钳制,妄图把广大沦陷区变成所谓“王道乐土”,而真实呈现在历史帷幕上的则是一幅幅血淋淋的“人间活地狱”……
这一年初春,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取道西安,将重庆国民政府发放给八路军的军饷带回延安,这也成了抗战中重庆政府发放给八路军的最后一笔军饷,因为国共关系的恶化已经从桌底端上了台面。
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首次提出了“曲线救国”一词,为自己的部下国民党军驻防文安、新镇的柴恩波部投降日军辩护:“现该部为保存实力及实施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日,实际仍为本党做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队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击也。”此论一出,立刻受到处于敌后和敌我交叉地带的国民党军的追捧,接替沈鸿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牟中珩叮嘱其部下:宁当伪军,别干八路。高升为鲁苏战区副司令的沈鸿烈也叫嚣着:反共第一,抗日第二;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国共合作的蜜月期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悄悄结束。具体到冀鲁边区的情况,国民党顽固派和投降派见八路军主力转移,边区根据地日见困窘,遂趁机掀起新一轮反共逆流,对八路军、游击队大打出手,妄图将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华北版图上彻底抹掉。
针对这种形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表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文章,严厉地指出:“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
周贯五看完这篇文章后,血脉偾张,胸中块垒随之释然。当时他正着手恢复边区的建设,方方面面进展颇为顺利,只是国民党的顽军时时干扰我军政策、法令的推行,动辄逮捕、杀害我抗日军民。为维护统一战线政策,边区军政委员会一忍再忍,但忍让总是有限度的,怎样把握这个限度呢?这正是周贯五倍感苦恼的地方,而现在,这个限度清晰地划出来了。
他把目光投向地图上河北省吴桥县国民党民军第二路张国基的地盘上……